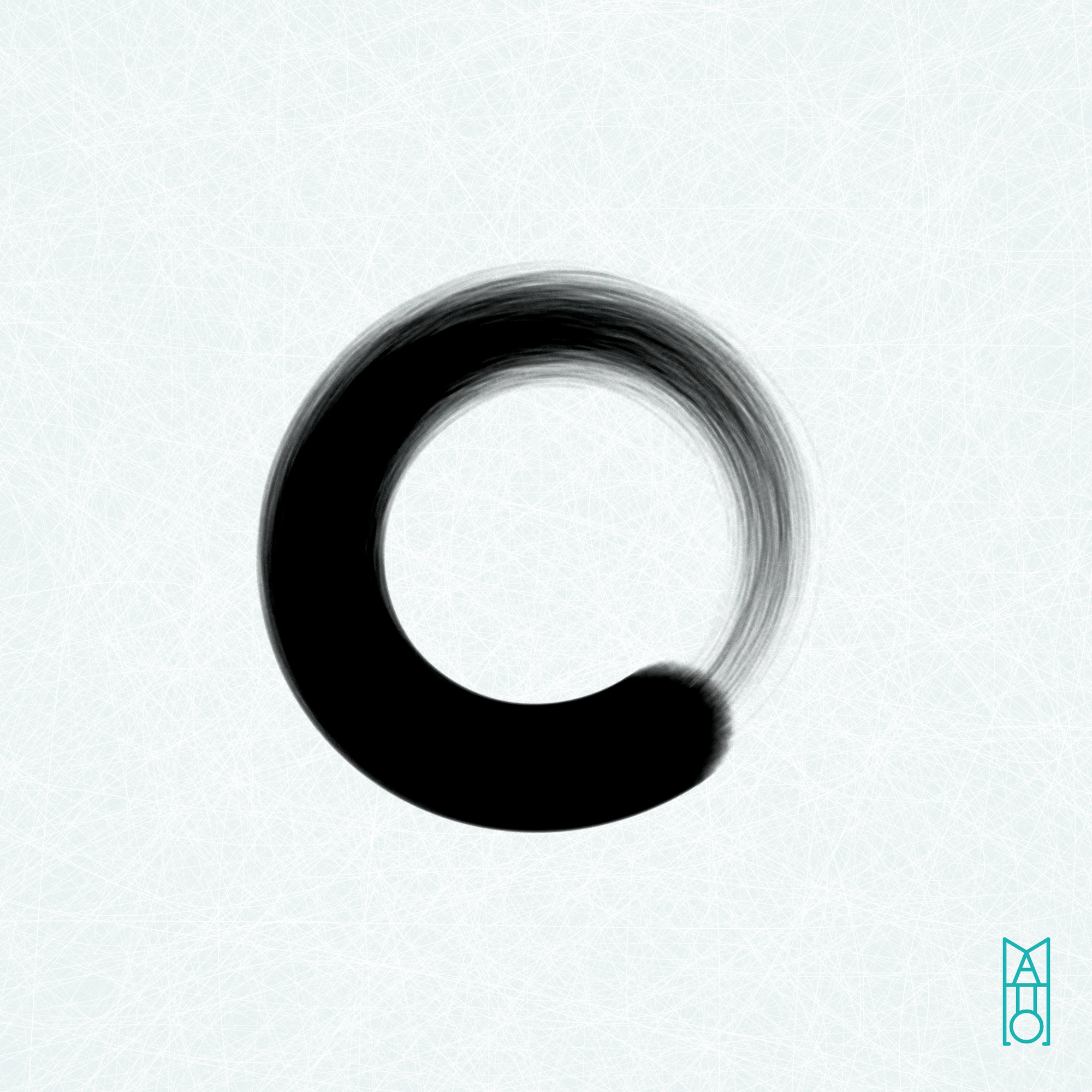對 Palantir 的回望 — 八年任期的回顧
作者:Nabeel S. Qureshi 原文在這,翻譯以下:
Palantir 現在很火。公司剛加入 S&P 500,股價一路猛漲,市值逼近 1000 億美元。創投們追著前 Palantir 創業者要投資。
對公司裡的老員工與校友而言,這種感覺很奇妙。尤其在 2016–2020 那幾年,說自己在 Palantir 上班並不受歡迎。公司被視為間諜科技、NSA 監控,甚至更糟。公司門口經常有抗議。即便是那些在道德上不反感的人,也常把它貶為打著軟體旗號的顧問公司,或者,頂多是一種精緻的人才套利。
我去年離職,但從未公開寫過自己在那裡學到什麼。關於這家公司,其實有很多外界不理解的地方。作為一個待了八年的人,這是我試著把一些事情說清楚。
(註:本文完全代表個人,和公司已無正式關係。我持有 $PLTR 多頭部位。)
1. 為何加入
我在 2015 年夏天加入,一開始在新開的倫敦辦公室,之後搬到矽谷,最後到華府,職位是前線部署工程師(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, FDE)。當時公司約 1500 人,辦公室在帕羅奧圖(總部)、紐約、倫敦與其他幾個地方。(如今約 4000 人,總部在丹佛。)
為什麼加入?
首先,我想在「困難」產業裡做真正重要的問題。出於個人原因,我關注醫療與生物,當時公司在這塊剛起步。公司談的是醫療、航太、製造、資安等產業——這些在我看來非常重要,但當時鮮有人碰。那時最熱門的是社群(Facebook、LinkedIn、Quora 等)和各種 C 端應用(Dropbox、Uber、Airbnb),很少有公司處理經濟裡真正棘手的部門。如果你想在這些「更難」的領域工作,同時又想要矽谷型的工作文化,Palantir 有一段時間基本上是唯一選擇。
我的目標是創業,但我想先(1)在這些產業之一扎深、學到真東西;(2)在一家美國公司工作,並透過它拿到綠卡。Palantir 兩者都提供,選擇就容易了。
其次是人才密度。我和幾位醫療垂直的早期成員(Nick Perry、Lekan Wang、Andrew Girvin)聊過,印象極佳。又面了幾位早期的商業運營與策略同事,更為折服。他們非常強烈、好勝、想贏,是名副其實的信徒;同時也很怪、很迷人——閒暇讀哲學、吃奇怪的飲食、為了好玩能騎 100 英里單車。這種基調其實承襲自 PayPal 幫。Yishan Wong(早期 PayPal)談過強度的重要性:
「總的來說,我看了更多新創後發現,PayPal 的人才水準未必比矽谷創業公司常見的人才更高,但不同之處或許在於自上而下的強度:Peter Thiel 和 Max Levchin 都極為強烈——超級好勝、勤奮、不肯認輸。這種領導能把『標準的』有才團隊推到能做出偉大事情,也因此孕育出後續成就的泉源。」
Palantir 異常強烈、也異常怪。我第一次和 Stephen Cohen 談話時,他辦公室空調開到 60°F,放著幾個奇怪的裝置來降低室內 CO₂,桌上杯子裡堆滿碎冰。整場對話他都在嚼冰塊。(據說對認知有益。)
我也和 CEO Alex Karp 面談,及其他領導團隊成員。我不需說服你 Karp 有多怪——看一段訪談就知道。我不能講我們聊了什麼,但他 2012 年的一段訪談很能代表他的風格:
「我喜歡在沒有任何資料的情況下見候選人:沒有履歷、沒有預談或職缺描述,就只有我和對方在房裡。我會問一個相當隨機、和他在 Palantir 要做的事不相干的問題。然後看他怎麼拆解,看他能不能意識到看待同一件事有好多種方式。我喜歡把面試保持很短,大約 10 分鐘。否則人們會進入他們學來的標準應答,你就看不出他真正是誰。」
我的面試往往與工作或軟體無關——有一次我們花一小時在聊維根斯坦。注意 Peter Thiel 和 Alex Karp 都是哲學背景。Thiel 的課堂筆記(https://blakemasters.tumblr.com/peter-thiels-cs183-startup)不久前剛流出,談莎士比亞、托爾斯泰、吉拉爾(當時冷門、如今成了陳腔)等等。
這種「知性上的自大」加上「強烈競爭心」的組合對我而言很對味。其實到今天仍難得——很多人複製了「硬核」文化與「這裡是海軍陸戰隊」的氣場,但很少有相應的思想氛圍、那種置身豐富思想脈絡中的感覺。這很難裝出來——你的創辦人與早期員工必須真的有思想深度。今天把這兩者都做好的公司,我想到的是 OpenAI 與 Anthropic。不意外,它們是人才磁鐵。¹
2. 前線部署
我加入時,Palantir 的工程師大致分兩類:
- 與客戶一起工作的工程師,稱作 FDE(前線部署工程師)。
- 在核心產品團隊(Product Development,PD)工作的工程師,鮮少拜訪客戶。
FDE 通常被期待「進駐」客戶現場,每週 3–4 天在對方辦公室,意味著大量差旅。對矽谷公司來說,這非常罕見。
這個模式有很多可談,但核心是:你在困難產業(製造、醫療、情報、航太等)中獲得對業務流程的細膩理解,然後用這些理解去設計真正解決問題的軟體。PD 工程師會把 FDE 打造的東西「產品化」,更一般地說,打造能讓 FDE 做事更快更好的軟體槓桿。²
Foundry 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這樣成形:FDE 到客戶現場,得手工處理一堆繁瑣事,PD 就打造工具把繁瑣自動化。要從 SAP 或 AWS 導入資料?有 Magritte(資料匯入工具)。要視覺化?有 Contour(點選式視覺化工具)。要快速起一個 Web App?有 Workshop(類似 Retool 的 UI)。久而久之,你就有了一套很棒的工具,圍繞著「把資料整合起來並讓它有用」的鬆散主題。
當時,允許客戶直接使用這些工具被視為一個激進的決定——它們還不太成熟——但今天這驅動了公司 50% 以上的收入,也就是 Foundry。從這個角度看,Palantir 完成了罕見的「服務公司 → 產品公司」轉型:2016 年稱它為矽谷服務公司並非全然不對,但在 2024 年就大錯特錯,因為公司成功打造了企業資料平台,毛利率已說明一切——2023 年 80% 毛利,這是軟體的毛利。對比埃森哲:32%。
Tyler Cowen 有句極好的話:「情境是稀缺的」。你可以說,這是此模式的基本洞見。走進客戶現場——創業導師 Steve Blank 稱之為「走出辦公室」——讓你能捕捉他們工作的「默會知識」,而不是企業軟體常見、扁平化的「需求清單」模式。公司對此信到有點好笑:常常是一通電話來,你就要訂隔天一早飛去某個非常隨機的地方——文化偏好是「先上飛機,再問問題」。這導致差旅支出曾長期失控——我們不少人都拿到了美聯航 1K 或類似會籍——但也因此積累了強烈且長期的學習循環,終究有了回報。
我的第一個大型客戶是空中巴士(法國),我搬到土魯斯一年,每週四天在工廠和製造人員一起工作,協助把我們的軟體在那裡落地。
剛到土魯斯的第一個月,週末都飛不出去,因為空管每個週末都在罷工。歡迎來到法國。(開玩笑——法國很棒。還有,空巴的飛機真是工程導向的典範。CEO 一直都是受過航太工程訓練的人,不是某個 MBA。至於誰不是嘛……)
CEO 告訴我們,他最大的問題是 A350 產能提升。我們就直接針對這個問題做軟體。我常把它形容為「做飛機用的 Asana」。把各種資料來源——工單、缺件、品質問題(「不符合項」)——整合到一個漂亮介面,能勾選完成工作、看到其他團隊在做什麼、零件在哪、排程如何,等等。還能搜尋(包括模糊/語義搜尋)歷史品質問題,看看當時如何處理。這些對軟體人來說都算基本,但你懂企業軟體有多爛——把這些「最佳實務」的 UI 真的部署到真實世界,就威力驚人。這最後幫助推動了 A350 的產能衝刺,在維持高品質的前提下把製造節奏提升了 4 倍。
這讓軟體變得難以一句話描述——它不只是資料庫或試算表,而是針對那個具體問題的端到端解法,至於通不通用,先放一邊。你的工作是解決問題,不用太擔心過擬合;PD 的工作是把你建的東西抽象化,目標是賣到別處。
FDE 往往寫能「快速把事做成」的程式碼,禮貌地說,這通常代表技術債與各種 hack。PD 則寫能漂亮擴展、適用多場景、不會壞的軟體。公司的其中一個「秘密」是:要創造深度且可持續的企業價值,兩者缺一不可。FDE 通常痛閾高,還要有嵌入陌生企業、取得信任的社會與政治技巧,及高速的開發節奏——你得在一兩週內做出有價值的核,讓客戶知道你是來真的。這也受惠於客戶對大多數軟體承包商的期望極低——那些多半是在實作 SAP 或類似軟體,時間表動輒數年、採瀑布式。所以當一群 20 多歲的小孩衝進客戶現場,兩週內就做出能用的真軟體,人們會側目。
這個「雙引擎」模型非常有力。每個客戶團隊通常很小(4–5 人),高速且自治;團隊很多,都在快速學習,而核心產品團隊的任務就是把這些學到的東西沉澱到主平台。
當我們能在一個組織裡被允許開展時,這往往很有效。阻礙多半是政治性的。每當你看到政府再給德勤一筆 1.1 億美元的合約做一個用不了的網站,或 healthcare.gov 那種慘劇,或舊金山聯合學區砸 4000 萬做一個仍跑不動的薪酬系統,你看到的就是政治戰勝了實質。再看 SpaceX vs. NASA 也是一樣。
世界需要更多像 SpaceX、Palantir 這樣靠執行差異化的公司——以達成結果為準,不靠玩政治,或只做一些無法命中目標的窄點方案。
3. 祕訣
FDE 做的另一件關鍵事是資料整合——光聽名詞就讓人想睡。但這(至今也是)是公司的核心,多年來外界一直低估它的重要性。事實上直到 AI 興起,人們才開始意識到擁有乾淨、整理過、容易存取的企業資料有多重要。(參見:AI 模型中的「它」其實就是資料集。)
簡單說,「資料整合」是指:(a)取得企業資料存取權,往往要和組織裡的「資料擁有者」協商;(b)清理並在必要時轉換,使之可用;(c)把它放到所有人都能取用的地方。Palantir 主平台(Foundry)裡許多底層、基礎的軟體,就是用來讓這些任務更快更容易。
為什麼資料整合很難?資料往往存在機器不易分析的格式——PDF、筆記本、Excel(天啊,太多 Excel)等等。但真正的絆腳石常常是組織政治:某個團隊或部門控制著關鍵資料源,他們之所以存在,就是這個資料源的看門人,而他們在公司裡往往靠提供該資料的分析來證明自己的價值。³ 這種政治角力會是巨大的障礙,有時結果可笑——公司買了 8–12 週的試點,我們前 8–12 週都在搞資料權限,最後一週瘋狂拼一個能 demo 的東西。
Palantir 早早意識到的另一個「祕訣」是:資料存取之爭部分來自真實的資安顧慮,而你可以透過把安全控制內建到平台的資料整合層——在所有層級——來緩解。這意味著基於角色的存取控制(RBAC)、列級策略、安全標記、稽核軌跡,還有一大堆其他資料安全功能,其他公司至今還在追。因為這些功能,導入 Palantir 往往會讓公司的資料更安全,不是更不安全。⁴
4. 關於文化
整體「氛圍」更像一個救世教而非一般軟體公司。但重要的是,這裡對批評極為包容、甚至歡迎——有人給我看過一串郵件:一位新進軟體工程師和一位公司 Director 在全公司(當時約千人)抄送的情況下公開、激烈地爭論。對一個理性主義腦袋、哲學畢業的我,這點極其重要——我不想加入一個不容批判的教團。但一個由在意事情、愛思辨的人組成、願意爭論世界往哪去、軟體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——甚至關乎存在論的——教團,就很吸引我。⁵
不確定現在是否還有,但當時你入職會拿到幾本書:《即興》(Impro)、《定時炸彈——蓋達與 9/11 之路》(The Looming Tower)、《訪談用戶》(Interviewing Users)、《搞定》(Getting Things Done)。我還收過早期 PDF 版的 Ray Dalio《原則》。這些定了基調。《定時炸彈》顯而易見——公司部分是對 9/11 及其之後不可避免的公民自由侵蝕的回應而創,背景知識很重要。但為何是《即興》?
要當一名成功的 FDE,需要一種對社會情境的格外敏感——你得和企業(或政府)裡最高層的對口合作並取得信任,這常常意味著要玩政治。《即興》之所以受宅宅歡迎,部分因它把社會行為機械化地拆解。公司的詞彙裡到處是《即興》的影子——例如「casting(選角)」。Johnstone 談到,同一個演員只要改變一些肢體行為,就能演出「高位」或「低位」:說話時頭保持不動是高位,左右晃動是低位;站得筆挺、雙手外顯是高位,駝背、手插口袋是低位,等等。如果你不懂這些,在客戶現場很難成功——也就很難整合資料、讓人用你的軟體——結果就是失敗。
這也是為什麼前 FDE 往往成為出色的創業者。(儘管 Google 員工是 Palantir 的 ~50 倍,但每一屆 YC 中,前 Palantir 創業者常比前 Googler 多。)好的創辦人本能地會讀場、讀群體動力與權力結構。這點很少被談到,但至關重要:創業成功本質上是在一場又一場的談判裡(整體上)取得勝利。招人、銷售、募資,本質都是談判。沒有這種對人類行為的直覺,很難談得好。Palantir 會教 FDE 這些,而其他矽谷公司很難學到。
另一點是 FDE 得擅長理解。你的效能和你多快能學會講客戶的語言、深挖他們的業務正相關。和醫院合作,你很快得能談容量管理、病患吞吐,而不是泛泛說「改善醫療」。藥物發現、醫療保險、資訊學、癌症免疫療法……各自都有專業術語,做得好的人往往學得快。
我很喜歡 Tyler Cowen 在《Talent》裡的一個洞見:最有天份的人傾向於發展出自己的詞彙與迷因,這些成為他建立的整個思想世界的入口。Tyler 自己就是例子。任何 MR 讀者都能立刻說出 10 個 Tyler-ism——「model this」「context is that which is scarce」「solve for the equilibrium」「the great stagnation」等等。還有其他擅長這點的人:Thiel、Elon(「multi-planetary species」「preserving the light of consciousness」等)、Trump、Yudkowsky、gwern、SSC、Paul Graham——他們經常創造迷因。這其實是影響力的良好代理指標。
公司也一樣。Palantir 有自己一整套龐大的術語,部分晦澀到「Palantir 到底在做什麼?」成了網路迷因。「ontology」是老字眼,還有「impl」「artist’s colony」「compounding」「the 36 chambers」「dots」「metabolizing pain」「gamma radiation」等等。重點不是解釋這些詞,每一個都壓縮了一整組豐富洞見;重點是:找公司時,挑那些有豐富內在詞彙、能幫你更有趣地思考的公司,錯不了。
提到 Palantir,多數人想到 Peter Thiel。但這些詞很多來自早期員工,特別是現在的總裁 Shyam Sankar。當然,Peter 對文化仍深具影響,儘管我在那段期間他並不參與日常營運。Joe Lonsdale 這份文件一度是內部文檔,後來公開,能讓你一窺這種文化原則。
(我想)另一個來自 Peter 的點是:不要給人頭銜。我在職時,除了少數幾位 Director 和 CEO,大家基本都叫「前線部署工程師」。偶爾有人自創頭銜(我認識一位自稱「Head of Special Situations」,笑死),但都沒流行起來。這很容易追溯到 Peter 的吉拉爾思想:一旦你創造頭銜,人們就開始覬覦它們,內鬥就來了,破壞公司內部的團結。還不如讓大家都叫一樣的職稱,把注意力放在目標上。
這種「扁平階層」當然也有好批評——《無結構之暴政》就是經典——而且在現代新創裡似乎不太流行了,很快你就會看到 CEO、COO、副總、創始工程師等滿天飛。但我的體驗是,它在 Palantir 運作得不錯。有人比別人有影響力,但影響力通常基於真正令人佩服的成就;而且最重要的是,沒有人可以命令別人做事。所以就算某個有影響力的人覺得你想法很蠢,你也可以無視,去把你認為對的東西做出來。文化還鼓勵這種人:故事會講某個工程師無視 Director,做出來的東西最後成了關鍵基礎設施,這會被樹為典範。
代價是,公司常常像沒有清晰戰略或方向,更像是一個培養皿:一群聰明人各自建立小封地、往各種方向亂衝。但它非常有生產力。外界低估了這家公司產出的新穎 UI 概念與想法有多少。今天非 Palantir 的等價物只出現了一部分,例如 Hex、Retool、Airflow 等都包含一些最早在 Palantir 開發的概念。現在公司在 AI 上也在做類似的事——面向大型企業部署 LLM 的工具非常強。
「沒有頭銜」也意味著公司內部誰紅誰黑換得很快。因為大家頭銜都一樣,你得用別的方法來判斷影響力,例如「最近誰跟這位 Director 很近」、「誰在帶看起來很重要的產品倡議」,而不是「他是某某副總」。結果就是一種大規模的英雄—狗熊雲霄飛車:某人紅一陣子,然後神秘消失、幾個月都看不到在做什麼,你也不會知道到底怎麼了。
5. 「蝙蝠訊號」
我把另一點歸功於 Peter:人才的「蝙蝠訊號」。我現在自己創業了(暫時低調),更能體會:招好人很難,你需要差異化的人才來源。如果你只和 Facebook/Google 搶同一批每年畢業的 Stanford CS,你會輸。你需要一批(a)偏好加入你而非其他公司的候選人,以及(b)一個能規模化觸達他們的方式。Palantir 有好幾組差異化的招募 alpha。
第一,早期那些支持國防/情報工作的人(在那並不時髦的年代),他們構成的人才池,會比平均更偏中西部或紅州出身的聰明工程師,也包括不少聰明的退伍軍人、CIA/NSA 出身者,想為美國服務,又看上矽谷公司的吸引力。我在公司第一天,內部 onboarding 時旁邊坐著一位看起來比我年長的同事。我問他來 Palantir 前做什麼。他面無表情看著我說:「我在那個機構做了 15 年。」接著我的第一位主管登場,他是俄亥俄州的前 SWAT 警、同時是退伍軍人。
這類人很多,且多半不會去 Google。Palantir 是他們唯一真正的「燈塔」,公司也高調支持軍隊、愛國等等,當時這非常不時髦,卻是一個非常有效、獨特的訊號。(如今有 Anduril,以及一堆國防與製造新創。)⁶
第二,你得夠怪才會想加入,至少在最初熱潮後(尤其川普時期公司成了賤民)。部分是早期激進的「使命導向」品牌調性(在當時不常見),也因公司明說:工時長、薪資低於市場、差旅很多。同時我們在矽谷校園徵才會被趕出去,只因我們做政府案。這一切都在篩選某種人:能自己思考、不會因一則壞新聞就過度反應的人。
6. 道德
道德問題令人著迷。公司毫不掩飾地親西方,我基本同意——更偏中國或俄羅斯的世界,在我看來更糟,而這就是當前的選擇。⁷ 活在自由國家的人容易批評自由國家,但當你真的體驗過另一邊(我童年有幾年在一個高壓國家),就沒這麼容易了。所以即便我不同意軍方做的某些事,我也不反對公司協助軍方。
但軍方有時會做壞事嗎?當然——我反對伊拉克戰爭。這觸及核心:在公司工作既不是 100% 善——因為我們有時會幫一些我不同意其目標的機構——也不是 100% 惡:政府做很多好事,幫他們用不爛的軟體更有效率地做事,是件高尚的事。澄清這個道德問題的一個方法,是把公司的工作粗分三類——不完美,但請忍耐:
- 道德中性:一般企業,例如 FedEx、CVS、金融公司、科技公司等等。有人可能反感,但大體上多數人可接受。
- 明確善:例如協助 CDC 的防疫、與 NCMEC 合作打兒童色情,等等。多數人會同意這是好事。
- 灰色地帶:牽涉棘手道德抉擇:醫療保險、移民執法、石油公司、軍隊、情報機構、警務/犯罪,等等。
每位工程師都面臨選擇:你可以去做 Google 搜尋或 Facebook 新聞動態,這些看起來都略微有益,基本屬於第 1 類。你也可以去做第 2 類,如 GiveDirectly 或 OpenPhilanthropy 之類。
對 Palantir 的關鍵指控似乎是:「你不該做第 3 類,因為有時會做出道德上壞的決策。」例子是 2016–2020 年間的移民執法,某些面向讓很多人不舒服。
但我看,完全忽視第 3 類、選擇抽離,也是種責任的放棄。第三類的機構必須存在。美國是由拿槍的人守衛的。警察必須執法——以我的經驗,即便有人對警務的某些面向道德不適,但一旦家裡被偷,往往第一時間就打給警察。石油公司必須提供能源。醫療保險每天都在做艱難決定。是的,這些都有不光彩的一面。但我們要完全抽離,讓它們自己搞定?
我不認為對是否與第三類客戶合作有一個清晰的普遍答案;個案判斷才是正解。Palantir 的答案大概是:「我們會和多數第三類機構合作,除非它們明顯是壞的,並相信民主進程會讓它們隨時間往好的方向趨勢。」於是:
- 關於 ICE,川普時期他們中止了與 ERO(Enforcement and Removal Operations,遣返作業) 的合作,但持續與 HSI(Homeland Security Investigations,國土安全調查局) 合作。
- 其他第三類機構多半合作,理由是它們在世界上做的整體仍是好事,儘管你容易指出它們也做過壞事。
細節我不便說,但 Palantir 軟體在阻止多起恐攻上部分居功。我相信光這點就能替這立場辯護。
這種立場讓很多人不舒服,正因為你無法保證自己所有時刻都在做 100% 善。某種程度上你任由歷史擺布;你在下注(a)做好事的總量大於壞事;(b)身在現場總比不在現場好。對我來說,這就足夠了。其他人會選擇去別處。
當然,這立場的風險是:它容易變成一個普適論證,合理化你去做任何權力結構要你做的事——你只是強化了既有流程。這就是為什麼我說要看個案:不存在一般答案,你得具體。就我個人而言,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做醫療與生物相關,我對自己的貢獻感到踏實。我打賭那些阻止恐攻的人對他們的貢獻也一樣如此;或在疫情期間分發藥物的人亦然。
即便風向已變、在這些「棘手」領域工作如今成了潮流,這些問題對科技人仍然相關。AI 就是好例子——很多人對 AI 部署的某些後果不安。也許 AI 會被用於駭客;也許深偽讓世界變糟;也許會造成失業。但 AI 也有巨大好處(Dario Amodei 近期一篇文章談得不錯)。
如同 Palantir,做 AI 可能既不是 100% 善,也不是 100% 惡。不參與——或喊停/暫停,這是幻想——恐怕不是最佳姿態。即便你不在 OpenAI 或 Anthropic,如果你有能力在 AI 相關議題上出力,你大概仍會想以某種方式參與。有些是容易的:做評估(evals)、做對齊、做社會韌性。但我的主張是:也值得涉入灰色地帶:做政府 AI 政策,讓 AI 進入像醫療這樣的領域。確實會很難。跳下去吧。⁸
回想今天在 AI 領域最有影響力的人,他們幾乎都在現場——不論在 AI 實驗室、政府,或具影響力的智庫。我寧願成為那樣的人,也不想當旁觀的高談闊論者。當然,這會牽涉艱難抉擇。但最好是當事情發生時你在房裡,即使之後你得離開並拉響警報。
7. 接下來呢?
我仍然看好這家公司嗎?是的。
這一輪 AI 週期的大部分生產力增益,將在 AI 開始為大型企業與產業提供槓桿時到來——製造、國防、物流、醫療等等。Palantir 花了十年與這些公司同行。未來,AI 代理(agents)會驅動許多核心業務工作流,而這些代理需要對關鍵業務資料有讀/寫的權限。把企業資料整合了十年,是把 AI 部署進企業的關鍵地基。機會巨大。
至於我,我正在執行期待已久的大計:創業。是的,會有政府相關的部分。團隊很棒,也確實在招人。我們偶爾也聊維根斯坦。
感謝 Rohit Krishnan、Tyler Cowen、Samir Unni、Sebastian Caliri、Mark Bissell 與 Vipul Shekhawat 對本文的回饋。
註釋
1
OpenAI 與 Palantir 都需要由有遠見且願意長期燒錢的富豪支持(分別是 Elon/YC Research 與 Peter Thiel)。Palantir 多年在政府市場掙扎,完全反其道於「精實創業」;OpenAI 也在數年裡(至少在聲勢上)被 DeepMind 壓著打,直到語言模型崛起。正如 Sam Altman 指出:
「OpenAI 做的每件事都和 YC 的建議相反。」
「我們花了四年半才推出產品;我們可能是矽谷史上資本密度最高的新創;我們在不知道客戶是誰或要拿來做什麼的情況下造技術。」
他還發了推文:「ChatGPT 沒有社交功能或內建分享,必須註冊才能用,沒有內建的病毒式迴圈等等。我開始嚴肅質疑我多年給新創的建議。」
這種關聯性確實存在:當你把公司放在賺錢之外的東西上(公民自由;AI 之神),你一開始吸引的是真正的信徒,他們反過來孕育出高度生成性的知識文化,等你終於成功時仍在。
不過這很難複製——你需要一位願景十足的億萬富翁,以及一個被忽視的經濟部門。2015 年的 AI/ML 不火;2003 年的 govtech 不火。
2
Ted Mabrey 關於 FDE 模式的文章寫得很好:
「這不是 FDE」(其 Substack 貼文)
3
同為前 Palantir 的 Sarah Constantin 在她精彩的文章裡更細談了這點:
「偉大的資料整合苦工」(Rough Diamonds 部落格)
4
題外話:媒體常把公司說成「資料公司」,更糟是「資料挖礦」公司。在我看來,這是單純的誤解。Palantir 幫客戶做資料整合,但資料屬於客戶——不是 Palantir。所謂「挖礦」通常是用別人的資料為自己牟利或拿去賣。Palantir 不做這事——客戶資料留在客戶手中。
5
正如 Byrne Hobart 在他對公司極具洞見的文章中指出:「『教』只是『用低於市場的薪水買到高於平均的員工留任』的委婉說法。」這也公平——公司薪資低於市場,待上 5+ 年很常見。當然,多數早期員工最後憑股票表現也過得不錯。但當時這不是顯而易見的;我們大多心裡把股權當作歸零。記得有張「解釋你股權價值」的小冊子算給你看如果公司值 1000 億時你會有多少,我們一群人還笑這太自大。寫稿時,公司市值 974 億美元。
6
順帶一提,公司從來不是什麼「右派反覺醒的前衛基地」。是的,意識形態光譜上什麼人都有,但我記憶中絕大多數同事都是正常的中間派。
7
在我看來,多數行動派低估了我們確實需要強大軍事這件事。我很好奇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,他們有多少人修正了看法——(Palantir 在烏克蘭的回應中扮演了關鍵角色)。
8
在 AI 安全這一側,Paul Christiano 就是例子——他去了政府,現在領導美國 AI 安全中心。
(完)